

罐罐茶:星汉西流夜未央
□吕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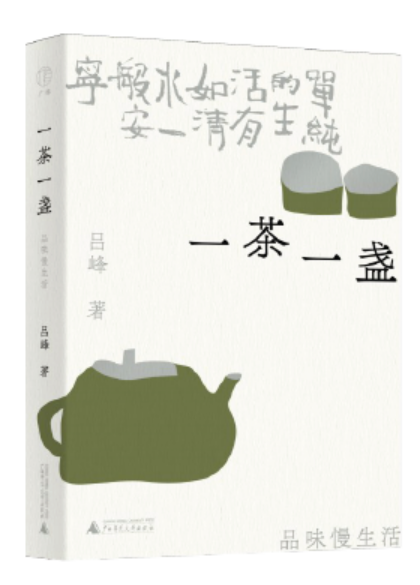
《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
著者:吕峰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风呼啸而过,黄土漫天,天地一片浑黄,这是我心中对大西北的印象。庚辰年秋,参加寻访黄河源活动,行至兰州,我因身体原因,只能原地休整。休整期间,彻底颠覆了我对大西北的刻板印象,一颗心亦为之动容。
借居兰州,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沿着黄河溜达,从早到晚;二是喝罐罐茶,亦从早到晚。不到黄河心不死。幼时,父亲动不动就念叨黄河,我觉得黄河实在是了不得。想象中,它如巨龙匍匐,它波浪翻滚,它汹涌澎湃。然而,兰州的黄河静谧、内敛,像田野上累极了的母亲,卧于蓝天白云之下,平和、从容、安详,只有喃喃的水声低诉着千年不息的秘密!
在河边溜达,早晚为宜。早上有晨曦可沐,黄昏有夕照可洇。初阳下,黄河若一把弯刀,光芒闪耀,常有鸟儿从河面飞过,像是云雀,叫声清脆,如钢琴的弹奏。它像受到某种昭示,昂首云霄,越飞越远,越飞越高,我的目光一直紧紧跟随,直至它消失天际。黄昏,夕阳像守财奴,悄悄藏起最后的金子。阳光一缕又一缕,像一条条细长的腿,在河面跳舞,雍容华贵。
溜达的次数多了,我结识了黄河边的筏子客。筏子客姓张,五十余岁,像极了我的父亲,发花白,脸黝黑,眼睛被皱纹簇拥,手指关节粗大,手背青筋突暴,掌上的纹路如刀刻。没客人时,他坐在河边喝茶,像一尊老去的泥塑,仿佛只要一阵风吹来,即会破碎开裂。茶是罐罐茶,一笼火,一撮茶,一个茶罐,两只茶盅,三五个红枣、桂圆,即他喝茶的全部家当。
罐罐倒上水,在炉子上烧。炉子为铁铸,可同时在炉边烤枣。水开了,枣也烤好了,将茶叶和烤好的枣投入罐中,继续煮,很快,汤沸,香逸,溢出的水“刺啦刺啦”地响。汤色如中药,浓而稠,香气迷人又诱人,其酽味胜过烈酒。罐罐茶需趁热喝,我一饮而尽,茶气浸透周身。喝罐罐茶,绿茶、红茶、黑茶均可,随个人喜好。张伯喜欢喝陕青茶,煮后,苦味浓郁,其味可在舌尖上停留许久。
罐罐为瓦罐,由陶土烧制而成,形状各异。罐罐本为褐色或黑色,加上经年的烟熏火燎,小小一物,有了烟火岁月的苍茫。我喜欢土陶,“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土是能给人安全感的物质,经水的搅拌,经火的缠绵,即可烧出陶,这是人近乎本能的创造。烧窑,动人之处在于窑变。三分人力,七分天意,有不可预料之惊喜,那亦是大自然的手笔,产生的美独一无二。
罐罐茶有提神醒脑之用,喝了它,干活儿才有劲。在张伯的印象中,他的祖辈、父辈早上起来即生火、烧水、捣茶,同时在炉边烤馍,七八片馒头干,即为早上的吃食。边吃边喝,很是享受。吃饱喝足了,方下地干活儿,或去黄河边摆筏子。到了晚上,才有余闲,好好地喝一罐茶。此时,喝茶方是消遣。柴火烧得“噼里啪啦”,脸烤得红彤彤的,不时地打着瞌睡,极为惬意。
“吹牛皮,渡黄河”,皮筏子是黄河特有的摆渡工具,以牛羊皮为囊,充气、扎缚、捆绑而成。彼时,人、牲畜、生活用资均通过筏子往返两岸。皮筏子是张伯的祖辈、父辈以及他谋生的工具,他大半辈子的时光也是在筏子上度过的。在黄河边摆渡皮筏子需谙熟水性,需有胆有识,需从容不迫,否则,万万不行。旧时,许多筏子客将命丢在了黄河的急流险滩中。筏子客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写照,饱含着艰辛,也显示着坚韧。
后来,皮筏子逐渐褪去摆渡工具的身份,不过游客来了,免不了要体验一番。远望,人与筏渺小成黑点,像一只在风浪里挣扎的蚂蚁,似乎一个浪就能将它吞噬。近了看,皮筏子随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而行,让人提心吊胆,实则四平八稳,有惊无险,颇有些“我自端坐,任他风浪”的味道。张伯是多年的老把式,险滩急流,惊涛骇浪,全在他的篙下化险为夷。坐于其上,河水从筏子的空当穿过,一伸手,一抬腿,即能撩到黄河水。
一天晚上,我宿于张伯家里。饭是在炕上吃的,一盘尖椒干豆腐,一盘洋芋擦擦,一盆炖小杂鱼,一大碗羊杂碎,一筐苞米面大饼子,再加上一坛子高粱酒。两杯酒下肚,我就半醉半醒了,也不知何时睡去。醒来,已是夜半,我鬼使神差地走出屋子,走到夜幕下,任如水的月光覆盖、洗涤,在千万座黄土塬的默视中,俯身趴在黄土地上,倾听着土地的心跳,感受着土地的体温。
夜凉,月亦冷。回到屋子里,无丝毫睡意。张伯正在烧水煮茶。对着秋月,我边喝茶,边神游。张伯见我对着月亮发呆,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亦奇怪,不知为何看见月亮总起思乡之情。可能是因出生在月光下,我对月亮有着莫名的亲近与熟悉。张伯唱起了花儿,同白天的花儿相比,晚上的花儿更能打动我。那声音发自肺腑,亦来自土地深处,夹带着黄土的腥甜味,听得我心里潮潮的、润润的。
火盆、火炉、火堆都是亲切的、温暖的。在茹毛饮血的年代,人的一切活动均围着火展开,烤火、烧水、煮饭、煮茶、熏山中野味,等等。对烧火,我是不陌生的,或者说是熟悉的。旧时,家里的灶台大大的,四四方方,里面嵌着一口大铁锅。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大铁锅在烈火中背负着一家老小的日常,联系着一家老小的冷暖饥饱。烧柴最怕湿柴,柴没干透,烟从灶口里“突突”地往外打,如火炮,呛得人咳嗽,咳嗽得头晕。
张伯的院子里堆满了坛坛罐罐,有喝茶的罐子,有腌咸菜的坛子,有盛粮食的大缸。它们于我,也是亲切的。幼时,一日三餐都靠咸菜下饭,咸菜坛子的存在如同锅碗瓢勺。坛中之菜随时节而定,春天只有香椿、青菜等寥寥几种,夏秋两季可选择的腌菜就多了,夏天有辣椒、黄瓜、苦瓜、大蒜、洋姜等,秋天则以萝卜、白菜、雪里蕻、芥菜等为主。坛子里时时都有咸菜,这样的、那样的,随吃随取。
罐罐茶是初时煮茶法的延续,可佐证《茶经》之记载:“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围炉煮茶,一炉火,一缕烟,一杯茶,三两好友,即可彻夜长谈。眼前的罐罐茶让我有些恍惚,朝代更迭,尘世沧桑,人更是微尘中的一粒,在时间的大风里来了又去,与之有关的人也渐如烟云消散,唯有一罐茶延续了初时之法,有初时之味,有初时之感受。
用得久的罐罐,有岁月沉淀下来的醇熟,哪怕是只烧白水,亦有直面而来的漫天芬芳,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喝罐罐茶,可听沸水之声,其声如奔雷,如海浪拍天,如暴雨滂沱,亦如远方山丘上,松涛阵阵。陆羽说煮水有三个阶段:水面起小泡,沸如鱼目,此为一沸;水面小泡如涌泉连珠,此为二沸;壶中沸水如腾波鼓浪,此为三沸。有的茶,一沸即可,有的茶则要二沸、三沸。
从兰州离开时,张伯送了我一个罐罐。回到家,用它来喝茶,总觉得差些味道。可见,对喝茶而言,情境何等重要。想着,何时再去大西北,再听一曲信天游或花儿,再坐一次皮筏子,再喝一次罐罐茶。
(选自《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