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聆听社会秩序变奏曲
□杨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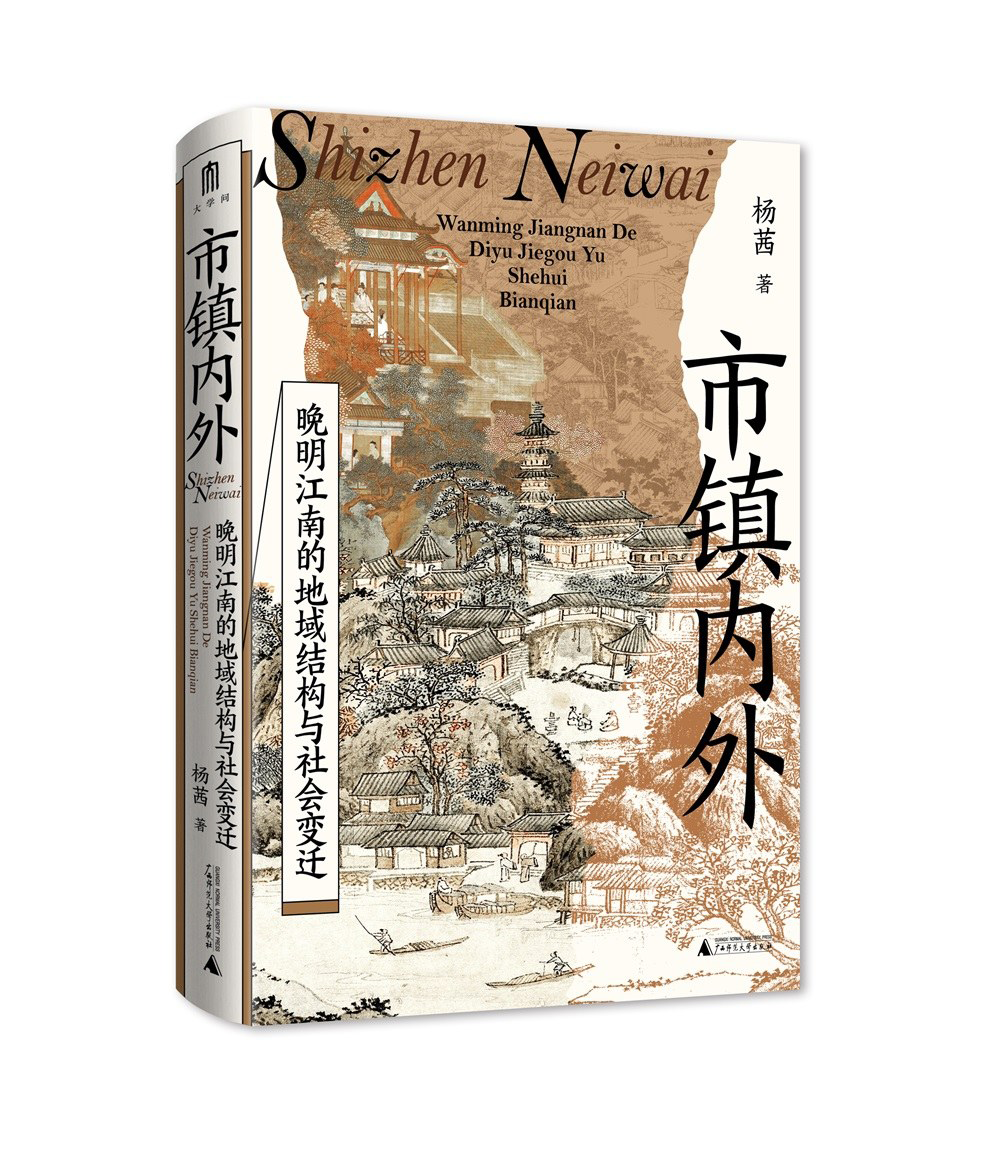
《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
作者:杨茜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聚焦晚明江南市镇的区域社会史著作,从家族兴替、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角度展开,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书中以权势阶层为切入点,深入市镇内部,揭示在带有明显人为“创市”痕迹的市镇中,权势群体的形成与变化,其中,地方力量的“士绅化”是一项关键节点;又从外部环境的视角,分析市镇这一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
本书将市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创新性地关注了地方力量在市镇发展中的作用,揭示特定时空下江南社会历史演进的内涵与特征,为理解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万历二十九年,常熟知县赵国琦主持县内的河道浚治,其中包含一条重要的地域性河道——横沥塘。该塘东接太仓七浦河,西抵白茆河,并流经常熟县内的何家市。何家市在明嘉靖年间即已出现,市镇中的商贾对外交通多依赖这条河道。赵知县在处理横沥塘疏浚工程时,对不同流经区域的役力安排做出明确区分,涉及人群除了惯例中的士大夫和农民,还特意提到了何家市中的“市民”:
白茆口迤至何家市,上区任之,市民向舟楫之利者佐之;由赤沙塘口迤至晋贤泾口,下区任之,别区如四十都、二十三都有田相续者佐之。……士大夫不得借优免之名,巧为规避;市商贾不得概诿为农氓之事,而坐享其嬴。(《邑侯赵公议浚横沥塘碑记》)
几年之后,另一位常熟知县耿橘再次开启水利工作。在浚治县中另一市镇(归家市)附近的河道时,镇中市民一度遭到奸豪大户的“仗役鲸吞”,耿橘为此发布公示,申明“止开市镇之河,略借市廛之民力耳”,强调“除市河之外,并不用市民开浚尺寸”。
通过上面两则事例,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在市镇中生活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已经是签派水利力役时的一个固定群体。与此同时,乡绅大户会像科派小农一样,向市镇“市民”转嫁劳役,但“市民”也有推诿逃役的情形。在乡绅大户和村落民众之外,市镇“市民”形成一方新的利益主体,而市镇本身也成为官府在牧民理政时必须予以单独考虑的一类聚落空间。
本书正是在诸多如上述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
16世纪之后,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市镇获得快速发展,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功能和规模也同步增长,其中一小部分市镇今天已被开发成为旅游区,如乌镇、南浔、周庄、同里、西塘、朱家角、枫泾等。这些热门旅游古镇,在明清时代都是具有重要市场功能的商品集散地,用著名学者施坚雅的话说,它们是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的出售地,也是家庭需用但不自产物品的购买地,换句话讲,商业市镇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所谓“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在江南地区以棉布和丝织品为大宗,它们从三角洲广大乡村生产者的手中汇集到一个个市镇,又从市镇店铺中卖出,随着无数客商“向上流动”进入全国乃至海外市场。
商业市镇的繁荣,是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突出表现。正因此,江南市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市镇的经济面貌是最受关注的层面。不过,当我于2012年前后开始接触江南市镇的研究话题时,却一直未打算在经济层面致力。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创作一份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市镇经济领域丰厚的研究成果令我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对历史中具体的人及他们的行动更感兴趣,尤其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许多冠以姓氏的市镇以及类似开篇的案例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其实,广布的市镇,在备受关注的经济领域之外,仍然对江南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思路下,本书的内容有两个锚点,一是生活于江南市镇中的“权势阶层”,二是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置于江南社会中展开讨论。
“权势阶层”,主要指豪强地主和乡绅大户,他们无论在明清时代还是现代学术研究中都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地方行政的完成有赖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发育过程中,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反映着一系列变迁。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内”的部分。
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来讨论,前提在于江南市镇乃自然生长而成,但并不具有建制性,所拥有的地理空间又往往地跨若干基层政区,且数量和功能都有相当的规模。本书主要选择以水利为主的州县治理工作,分析市镇作为这一时期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此时,市镇内普遍存在的权势阶层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外”的部分。
(本文为《市镇内外》自序,标题为编辑所加)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